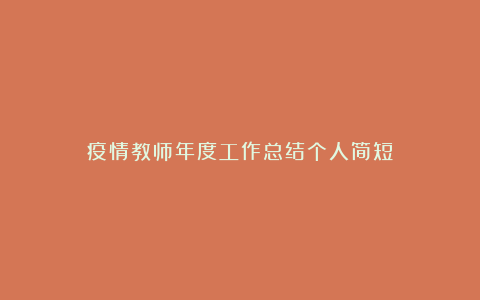病痛散文
- 文档
- 2024-09-06
- 158热度
- 0评论
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病痛散文,本文共4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病痛散文
刚届不惑,身体就大不如前。偏头痛,胃痛,颈椎痛,浑身酸痛,近日又添新疾,翻身和站立,腰部又出现难忍的`痛。医嘱为“腰椎间盘膨出”,要卧床休息,不能长久坐立,不能提重物,不能弯腰,一连串儿“不能”让我汗颜,更让我失去了行动自由。
平时工作忙,年休假“可望而不可及”,这回倒休了几天病假。卧床一周,烤电、推拿,总算重新站立起来。想当年,胃口好、身体棒,行动敏捷,干工作精力十足,没想到这么快就在健康问题上走上了下坡路。总听人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健康是1,其他为0,健康没了,什么都没有了”,现在终于有了切身感受。
病痛是一种难受的感觉,任何人都不愿意体验和承受。病痛除了先天疾病、遭遇灾祸等原因引发,更多是由于自己平时不注重锻炼,不注意保养,不会科学调节身心造成的。
病痛会影响心态。近两年我会经常想到“衰老”“死亡”这样的字眼儿,甚至爱听的歌曲里出现了《当你老了》《时间都去哪儿了》这样让人忧伤、让人感叹年华易逝的歌。病痛会影响与他人交往。白居易有一句“不缘眼痛兼身病,可是尊前第二人”,不能陪友人饮酒,多少会有些无奈吧!病痛难免衍生出坏心情,唐代诗人王建就发出“病多体痛无心力,更被头边药气熏”的感慨。
记此小文自警,同时祝福亲友们健康人生一百年。
病痛的夏日散文
从事写作十余年,我至今也没留下关于父亲的文字。也许是我这支笔太笨拙,写不出象样的东西。每次正下笔要写的时候,心里总有潮水在澎湃,泪水就不住地在眼眶里打转。写到一小段时,就草草收场,最终没写成。想不到再次下决心来写时,父亲早已随风而去。
那是二零零五年夏天,父亲被突然诊断出是肺癌,坚持了两个月的生命后,于六月十七日在痛苦中仙逝了。刚开始,父亲的症状表现为双手麻木,起初到乡里赤脚医生就医,都说是风湿性关节炎,治了很久也不见好转,而且手指慢慢地不能伸直,越来越没有知觉,吃饭时筷子也拿不稳。我们又带他到县人民医院作CT,医生诊断为颈椎病,于是又医了两个月,却仍然无效。我们不得不转院到南充市川北附属医院,作了目前较高级的全身检查――核磁共振。通过全身扫苗,终于发现在肺部长有恶性肿瘤。检查结果出来后,我和随行的姨父在办公室等待医生的病情分析。医生叹了一口气:“好年轻呀,才五十岁!”然后,姨父就让我到办公室外,和父亲一起都在门外等候。我心里突然间好象被冻结了,呼吸极困难。我理解医生的叹气声,也猜得到父亲的病很严重了,相信父亲大概也有所知觉,只是不言罢了。
当天回到家,姨父并没直接告诉我父亲的病情,我懂得他的意思,他怕我受不了打击。姨父为了给父亲作进一步确诊,于是我们又将他送到县医院拍X光片。影片出来了,我虽看不懂,但看得出影片上照出的肺部左边已雪白一片,模糊不清。医生说,这是肺癌晚期,最多活两个月。姨父告诉父亲,他得的是肺结核,不严重,能治好。而我却和姨母躲在医院的角落里痛哭,姨母说:“洪波,你要沉住气,你是长大了,不能让你爸知道,懂吗?”
我断定父亲知道我们骗他。因为他曾说对我说过:“孩子,你和弟弟都长大了,要好好地生活,以后要好好照顾妈妈,爸爸没尽到责任,没给你们成家!”当时,我的泪水就顺着往肚里流,我仍要强装笑脸对他说:“爸爸,你胡说什么呀,又不是世界末日到了,你的病没什么大不了,能治好!”
我不敢把病情告诉母亲,怕她沉受不住,但她还是知道了,天天都伤心欲绝,以泪洗面。父亲却出乎意料地劝她:“有什伤心的嘛?五十岁是死,八十岁也是死,我都不怕。”我知道父亲这句话的分量,他是那么乐观。
又过了一个多月,父亲的病情比想象的还恶化得快。虽然我买了抗癌药给他吃,每次都是我把药分好后给他喂,不能让他看到“癌”字字样。但再好的药又有何用呢?很快,父亲便卧床不起,一切都靠人护理。我知道父亲所剩的日子不多了。父亲每天都沉浸在痛苦中,在死亡线上挣扎,痛得历害时,发出的呻吟邻居家都能听见。有几次,父亲受不了,直叫我们给他喝农药,把他杀了算了。我的心里在隐隐作痛,像无数根钢针在扎,只好就给他打强力镇痛针――曲马多。
父亲直到去世,从来没见他掉过一滴泪,母亲却把泪水都哭干了,我们都劝她,怕她也哭垮了身体。
父亲的一生就一个字能概括――“苦”。听他讲,小时候他没有吃的,有一次把癞蛤蟆烧来吃,差一点被毒死。那时家里穷,又是吃集体粮,一年就分几十斤,要是在地里捡到几根红薯,也不敢在外张扬。没吃的的时候总吃干猪草、鹅儿草。为了改变家境,父亲与母亲开过窑厂,自己生产砖瓦,办过养蚕基地,最后都“破产”了。有了一点积蓄后,又与人和伙买了一辆拖拉机开,最后连本钱也亏掉,欠下一屁股债。在这样疾苦的'生活下,我那时却给父亲雪上加霜。不知从几岁起就生病,一直到九岁才全愈。我也不记得父亲有多少次背我东奔西跑,四处求医,更不知花了他多少钱,有几次差点就夭折了。听别人说,我是被父亲从死亡的边缘抢回来的,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可是我的后福在何处呢?父亲早早地就下我们一家三口,我还没来得及尽孝道,他就这样绝情的离开了。
父亲在世时,我常常听他说:“人不要做好逸恶劳的人,只要勤劳,就不会没饭吃。”的确,他也是这样做的,父亲一个人在外边挣钱养家,还要操劳一年四季的庄稼。母亲又经常手痛,做不得重活,家里五个人的田地,他一个人揽完。有时候,我觉得父亲怎么就像“铁人”一样。我也阻止过他,叫他少种点,够吃就行,可他老听不进去,把能够用的荒山都开辟出来种东种西。每到农忙季节,别家都请人帮忙,父亲却舍不得花钱,所有的活都与母亲两人分担。到夏天特热的时候,父亲就利用凉爽的夜晚在地里干活,干到凌晨两点多。
其实,父亲在病前就有过一回预兆,可谁都不曾察觉!他喜欢抽烟,去逝前一年有一次咳嗽非常历害,吵得晚上我们都不能入睡,但拿了药后隔一段日子就全好了。谁也意想不到,直到去逝前,父亲的肺一点都不痛,也从来不咳嗽,却长了肿瘤。医生说,癌症一般都在晚期才能发现,早中期又不痛,没有知觉。我知道,父亲是多么不愿离开我们,就像我们舍不得离开他一样,他那样地热爱生活,生活却对他如此不公!
写到这儿,我的泪水又开始在打转,双手发软,我不知哪儿来的勇气写完它,还是就此打住。不知父亲在九泉之下能否体悟到我对他的思念?不管怎样,我要用心永远记下父亲那难以磨灭的病痛的夏日!
爱,在病痛中沉沦散文
人生航行,经过一个又一个驿站,有时需要驻足停留,好好给自己找个沿岸的港口,让自己远行的心,抛锚停靠安歇,流年的季节未梢的告别,有太多的留恋,当这种留恋被遗憾层层包裹,内心深处的些许美好也会随之凋落枯萎。---紫蝶儿
近日的身体状况很不理想,越加严重的眼睛加上腰的疼痛,已经让我整夜的不能入睡,医生一再叮嘱不能再对着电脑,要卧床休息,然而,闲暇下来的我,还是会忍不住的打开电脑,会不自觉的打开音乐,听着这些熟悉的伤感音乐,打开空间、进入日志、敲打键盘、书写一些伤感的文字,如此都会在不知不觉的进行。
音乐,我喜欢那种唱到灵魂深处,冲去心灵尘埃的感受,在那飘然的意境里,置身万物混合的弥散,柔美而又忧郁的动感,随着忧感音韵的飘远,思念就会缠绵在飘渺的意境里,构造一个脱离世俗的境界,这一刻,尘封在回忆里的忧伤,随着安静的旋律悠然而行。雅独芳华,在音乐里,默默地想念一个人,都说流年如歌,时光如水,于是我学会用净水般的心情,用音乐来慰藉,找到自信,去除那些世俗的搅扰,音乐的飘渺里,去感受白云悠悠的天空,诠释音乐的心情,心存善念,感受音乐美的升华,感受音乐诗意的天使,感受人生的沧桑,感受时光的东流逝水。
情动的将笔又一次落在了空白的纸上,这或许,是一种习惯,是我长久以来,所戒不掉的生活习惯,一直用文字,记录着醉一程,醒一程的起起伏伏。也曾有人说,恋上伤感文字的女人,总是太过孤单和寂寞,而我却不这么认为,我有它们陪伴一点也不孤单也不寂寞。我是忧伤的,因为我独处的只有文字陪伴左右;我是幸福的,因为我还有我爱的文字可以陪伴左右。我总是在自己的世界,写着与自己无关的故事,与别人无关的心情,文字的能力有限很多感觉非笔墨可形容像伤心欲绝这种事你还可以讲得出来,那你还不算太过伤心。
内心曾有一张自己结的网,网不到别人的心,却缠绕了自己的忧伤,内心曾有一扇不愿开启的窗,里面住着不能回首的过往,内心曾有一则无形的屏障,看得见彼此的眼眸,却无法触摸彼此的目光,曾有一页不想翻过的日历,标志着某年、某月的某个地方有一本珍藏的日记,没有一个字,直叫人泪流千行,曾有一块石头,因为刻着莫人的名字,就一直把它当做宝,曾有一抹不能触碰的伤,就算是时间都不能治疗,曾有一个不能唤出的名字,纵使唇间呢喃千遍,最终不过空梦一场。
我知道我的软肋,是看不透、舍不得、输不起、放不下,看不透人际中的纠结、争斗后的隐伤,看不透喧嚣中的平淡、繁华后的宁静;舍不得曾经的精彩、不逮的岁月,舍不得居高时的虚荣、得意处的掌声;输不起一段情感之失,输不起一截人生之败;放不下已经走远的人与事,放不下早已尘封的是与非。我也知道再执着的未来,也会有以往;再优美的旋律,也会有情殇;再期盼的目光,也会有迷惘;再纯净的文字,也会有悲伤;再动人的风花雪月,也等不到地久天长。
生活如一段录音,倾听午夜的独白,纵情灵魂的舞蹈;记忆如一截儿歌,纯真绚烂的往事,珍藏曾经的童谣;命运如一株蒿草,笑看天空的变幻,固守无助的孤傲;抗争如一炉焦炭,灼痛世俗的目光,驱赶生命的奔跑;生命的轮回有聚有散,站在流年的彼岸,回首那逝去的光阴,岁月是记忆的沙漏,留下的只是拼凑的片段,每一个片段都值得珍藏,每一段岁月都值得难忘,茫茫人海,相遇就是一种缘份,每一次遇见,都是一场美丽的邂逅,每一次聚散,都是一种命运的注定。
红尘陌上,百媚千红,只是写意的一处风景,人生有无数的驿站,微笑着遇见,微笑着与过往道别离,伸手,捡拾一片爱的花瓣,为你,储存一抹心香,让生命,在遇见里欣喜,让眼眸,在芬芳中嫣然,多少年华如水,将执念写成铭心刻骨,多少过往成诗,将流水落花写成美丽。也许,一条幽径,曲折迂回中总会激起心旷神怡的向往;一波巨澜,潮起潮落时更能叠出惊心动魄的鸣响;一个故事,遗憾悲婉里才有肝肠寸段的凄凉;一种人生,跌宕困顿中方显惊世骇俗的豪壮。
熟知,浅笑离愁,婉转牵绊,就好像悲伤这场盛宴,曾在无数的.执念中,写满了太多的泪痕,在流年荒芜的画里,一笑而过,那些缘深缘浅终将缘来缘去,彻悟了思情的逐情,世间并没有天长地久,地老天荒,那些曾一段华丽的对望,是悲伤里浅笑的云卷云舒,花开花落。时光太瘦,指缝太宽,一个不经意,流年已把故事写好了结局,有些人注定要消散在清风明月里,有些缘注定要飘零在落花流水间,再怎么刻骨铭心的记忆,也总有一天被光阴的风吹散的无影无踪,想再一次见到安好的模样,只为确定你尘埃落定的幸福,从此,天涯陌路,后会无期。
一路走来,爱过喜欢过的人,走散了一些,失去了一些,存留下来的这一部分,应该去珍惜而不是去逃避,总觉得自己不够好到底是哪里不好呢!做着自己喜欢的事,认真过的一些事,却从来都是不温不火;所谓色相,所谓家世,也总觉自己没有;疏懒,被动,慢热的秉性,这一辈子怕是也改不了了,认为这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是成功的人生,但是我只想告诉自己,这也不是失败的人生,这只是,某一种人生。那些曾经走过的悲喜,刻成了回忆,每个不经意想起的瞬间,都在回忆里面留下伤痕,多余的感伤都该被淘汰,有些事或许该要学会看开,有些人或许该要学会原谅;现实太残忍,对别人少了那一种信任,世界太复杂,对自己少了那一种单纯。
喜欢美丽带点忧伤的文字,只是喜欢,没有沉溺,喜欢音乐,因为音乐是最忠实的朋友,可以在其世界自由驰骋,暂时忘却喧嚣,在婆娑的岁月里,一抹相思锁浮华。爱,在文字里缠绵,情,在文字里窖藏,任流年似水,匆匆而过;思念,在音乐里痴缠,牵念,在音乐里徘徊。告诉自己,笑着面对,不去埋怨,悠然,随性,随缘,注定让一生改变的,只在百年后,那一朵花开的时间;在流年尽逝的记忆里,每个人的生命只是沧海之一栗,承载了太多的情非得已、聚散离首,天各一方,情深意浓,思念起来是遗憾的伤感垂泪,青春不在,颜衰色旧,感叹起来到也是遗憾的潸然泪下。
记忆是风,舒缓了病痛散文
大山上的树已经长得很是茂密和壮硕了,走在山林中,风是不停地在吹着的,冬日的暖阳透过叶子照在身上很暖和,风也变得格外的温柔,叶子照旧是沙沙地响着,间或传来一两声凄厉的不知名的鸟儿的叫声,一切都和二十年前一模一样,仿佛从来都有这般的气息,混着雨后泥土的湿甜味,被那几十年来恒而未变的风带到了记忆的远方,而那时候,外公也正像这些树,高大结实,从不向困难低下头颅。
这个故事是外公外婆亲口对我说的,在那个狭小的、充满药水味的、几乎要与世隔绝的屋子里,两个颤颤巍巍的老人用他们并不顺畅的声音讲述了他们的一生,我的眼里几乎要噙满泪水,而老人却显得异常的轻松,身上也不那么疼痛了,呼吸似乎都匀畅了许多。于是我便决定要用文字把这些记忆保留下来,以作深切地企盼。
记忆追溯到了1938年,那是一个于我们而言非常遥远的年代,我看《平凡的世界》时总是会习惯性地联想在故事开始的1975年我的亲人们可能在做什么,这也使得我阅读作品变得有意思多了。而1938年的我仅能联想起的唯一记忆便是历史书上记录的抗日战争,脑海里瞬间充满了电视剧里枪林弹雨、硝烟滚滚的那些拼杀的场面。而就是在这么一个动荡的年代,外公出生了,他是个遗腹子,父亲在他即将出生的前一个月去当兵了,而不久便从前线老乡那传来战死的噩耗,没过多久,母亲也因伤心过度也去世了。从此外公便和奶奶过起了挖野菜和放牛的相依为命的生活,以致儿时的记忆永远充斥着野菜根的苦涩味和牛身上的尿骚味,虽然日子艰苦得令人难以想象,但有至亲陪伴却成了外公最大的乐事。可当放牛郎长到十几岁时,奶奶在一个寻常的晚上停止了呼吸,未谙世事的他还未认识到“死亡”这一名词的实际意义,直到奶奶身体便得冰冷僵硬,直到他一遍又一遍的呼唤声变为徒劳,他终于想起不久前奶奶说的“要走了”是什么意思,也得到了这么多年来一直问奶奶自己的父母去哪儿了的确切答案。这时候,他才意识到“死”到底有多可怕!
他成了一个彻底的孤儿了,再也没有人会在燥热的夏夜为他扇扇子赶蚊子了,在寒冷的`冬日为他暖好被衾了,他只有一个人,孤孤单单地活着。他还是会去给人家放牛,帮堂亲做工,以此来换得生存的物资,尽管经常是饱一顿饥一顿,但他仍然要好好地活下去,这是奶奶告诫的。他一直很听奶奶的话。
后来,他学会了用牛耕田,外公就和他的牛作伴,每日早出晚归,人和牛一样,在夕阳下耕着犁,拉开了一条斜长的身影,暗晖在田间慢慢移动。
外公的勤劳忠厚终于在那个信息沟通并不发达的年代传遍了前后村庄,这个身子壮实、长相清秀、吃苦耐劳的后生被外婆的父亲看中,于是他们就在一间狭小的土房里开始有了自己的家,还有那一床红色的鸳鸯被。日子过得简单而甜蜜,男人用自己天生的力气和毅力支撑着这个家的大梁,女人则用自己的温柔和耐心为他生儿育女。外婆一向体弱多病,却是外公用自己的脊梁将整个家撑起,用自己的臂膀挽着她熬过了一次次病痛的折磨,儿时太少的亲情滋润让他更加懂得如何用生命去爱一个人。白天,他几乎都是在劳动,不管年代如何变化,他就像是扎根在村庄里的大树一般,守护着整个家;晚上,他经常是一边帮外婆熬着药,一边看着外婆给他破旧的衣服又打上一个新的补丁,借着微弱的油灯光,外婆眯着眼,一针一针地缝补着,床上正躺着三个可爱的熟睡着的孩子,外公感到自己很幸福,也眯着眼笑。
孩子们终于长大了,儿子考上了大学,外公外婆高兴坏了,可是一想到高额的学费,他们又开始发愁了,咬着牙将山上的大树砍掉换取了一笔学费,东拼西凑几乎找遍了所有亲朋好友,终于让舅舅得以顺利毕业。此时的他们,皱纹不知在何时已经深深刻在了他们的脸上,像烙印一般。
生活在进入2000年以后开始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子虽然过越来越好,但他无法融入大城市的生活,拒绝去舅舅家养老。只有外婆知道,他是离不开这片土地、离不得那座山啊。只要一得空,外公仍然像往常一样扛着锄头去地里,哪怕只是除除草,或是拿一把镰刀束在腰间上山,砍不动树了就伐伐杂草杂树,精心呵护他一手栽下的小树,因为在舅舅上大学那年,壮硕的树都被砍了。外公想要看着它们长大。
他们的日子又回到了刚刚结婚的时候,两个人守着自己的土地、守着那片杉树林,他们以为这样的日子还可以过很久,起码外公觉得可以看到那些树长成参天大树的。可是现在,外公病了,像做活累垮了的牛,像枯了桩的树,说话儿都喘着粗气,身子也佝偻着,外公说,自己也快“要走了”。
不可控的癌细胞渐渐附着在他的体内,也附着在她的心上,他们都意识到生命之至末路了。他住院,她寸步不离陪在身侧;他咳嗽想要吐痰,她立刻像条件反射一样拿好纸巾和痰盂;他打点滴手冰凉冰凉,她提前充好热水袋用自己满是褶子的手轻轻地把他瘦骨嶙峋的被扎过无数针眼的同样满是褶子的手放进热水袋的暖夹层中……他想说话儿,她陪他回忆往事,用记忆疗伤;他身体乏力不想言语,她也在旁边无言地陪伴着。
我是在病房听着他们的述说的,故事真实得让人心痛,他不是电影里的人物,只为博得观众一时的泪水,他是我的外公,他那看似很平凡的一生,却让我的心久久地像针扎了一般地疼。
趁着假期的空闲我爬上了那座山,树木看起来已经很壮硕了,风在吹着,混着泥土味,和外公描述的二十年前的画面一模一样,站在山上,我可以很分明地看见村庄的炊烟。我闭上眼祈祷,希望奇迹能够发生。虽然我几乎都要相信外公已经没有力气再上山的这个事实了。
就在前两天,天气也比往常好多了,外公看起来也有了些精神,老伴随口说了句自己嘴唇好像开裂了,然后我看见外公默默地戴起了帽子,换着鞋,我问外公去哪儿,他穿好鞋后头也不回地说了句“买药去”便弓着背走了。这就是外公,这么多年来,似乎给外婆买药已经成了习惯,成了条件反射,成了一种毋庸置疑的默契,以至于忘了自己也是个病人。
★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