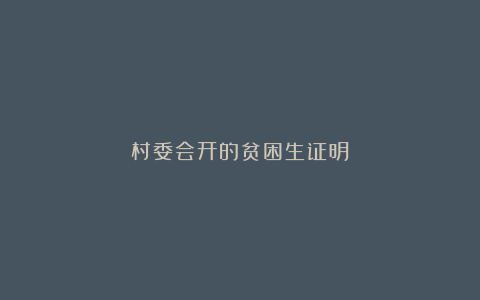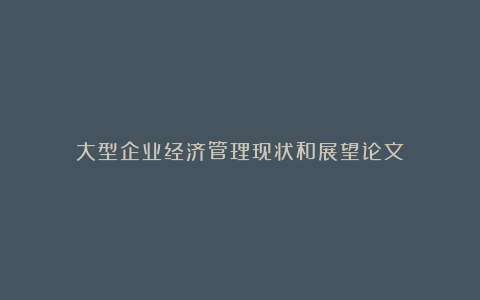《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萨满文化
- 文档
- 2024-07-21
- 163热度
- 0评论
下面是小编给各位读者分享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萨满文化,欢迎大家分享。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萨满文化
萨满教作为一个古老的原始宗教,在北方民间流传甚广。
《额尔古纳河右岸》向我们展现了鄂温克游牧民族的百年沧桑。而小说中描写的拥有神力的萨满又为这个民族增添了一分神秘。萨满教的神歌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也最具有文学价值。以鄂温克族为例,无论喜事丧事,大小节日还是治病救人,都会有萨满的身影,只要有他们出席的地方,就会有神歌。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妮浩身为萨满救人是她的职责,但她又是位母亲,每救一人就会使她失去一个孩子,这对身为母亲的她来说是痛苦而艰难的。她为每个离她而去孩子唱起神歌,愿他们的灵魂能够通往天堂。果格力是妮浩的第一个孩子,也是最先离开她的孩子,妮浩将夭折的果格力装进白布口袋,扔到向阳的山坡,为果格力唱了最后一只神歌:
孩子呀,孩子,你千万不要到地层中
去呀,那里没有阳光,是那么的寒冷,
孩子呀,孩子,你要是去就到天上去
呀,那里有光明,有闪亮的银河,
让你饲养者神鹿。
妮浩失去的第二个孩子,是她最爱的百合花――交库托坎。而她要救的人却是人人都讨厌触犯神灵的马粪包。妮浩要为救这样的人而失去她的百合花,妮浩穿上这身神衣,想必是如山一般压在她的身上,又如火一般烧着她。马粪包被救活,可可爱的百合花却凋谢了。妮浩为她的百合花唱起神歌:
太阳睡觉去了,林中没有光
明了,星星还没有出来,风
把树吹的呜呜响了。我的百
合花呀,秋天还没到来,你
还有那么多的美好夏日,
怎么就让自己的'花瓣凋零了呢?你落了,
太阳也跟着落了,可你的芳香不落,
月亮还会升起![2]
两个孩子接连失去,对妮浩来说是巨大的打击,她身上有萨满的职责,可她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像驯鹿那样,为救人而失去自己的生命。当耶尔尼斯列同样是因此而失去生命时,妮浩除了惋惜、悲伤又多了一种情绪――愤怒。她为耶尔尼斯列唱的神歌是这样的:
世上的白布口袋呀,你为什么不
装粮食和肉干,偏偏要把我的百
合花揉碎了,将我的黑桦树劈断
了,装在你肮脏的口袋里啊!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还有唱熊祖母、玛鲁王的神歌,还有小说结束后对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歌唱。总的来说,萨满神歌的内容,按祭祀仪式可分为家神神歌和大神神歌。[2]这些神歌多是口头创作,表达当时的思想感情。神歌尽管在表层结构笼罩着宗教色彩,但是从诗歌的结构、语言、韵律等方面来讨论的话,比较接近民歌体的诗。鄂温克族萨满神歌是鄂温克族古代文化的经典之作,尽展鄂温克族古代宗教文化,音乐文化,舞蹈文化与诗歌文化之原声岁月。
萨满教与其他宗教相比,萨满教并非信仰一个神,他们的信仰神非常多,虽然他们信仰的神很多,但从总体上看主要分为两类,一是自然当中的神,二是动物神。萨满教认为世界万物皆有生命的,即“万物有灵”。
首先是他们对大自然的崇拜。他们认为山有“山神”,水有“水神”,打雷有“雷神”,火中有“火神”,树有“树神”等。这些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均由体现,例如,他们从不往火里乱扔东西;在山中走路时不大声说话,怕惊扰到“白那查(山神)”;看见树身上有“白那查”的“脸”,不仅要下跪磕头,还要敬烟敬酒,拆枪械弹,将猎到的猎物的血涂在“白那查”的嘴上,以求山神保佑他们。
其次是他们对动物的崇拜。他们主要崇拜两种动物一个是熊,另一个是狐狸。他们对熊的崇拜主要表现在他们吃熊肉之前要学乌鸦的叫声叫上一阵,让熊知道是乌鸦吃了它的肉,还要为这只熊举行风葬仪式,为它唱神歌;吃熊肉用的刀,无论有多锋利,他们都把那刀叫做“刻尔根基”,意思是“钝刀”;吃剩的熊骨头也不能乱扔,马粪包就因在吃熊肉时乱说话,乱扔熊骨头而险些丧命。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并没有对狐狸没有太多的描写,只有一写了狐狸,是在伊万的葬礼上,突然出现两个浑身素白的姑娘,自称是伊万的干女儿,有人说这两个姑娘就是伊万曾经放过的那对给他下跪,跟伊万作揖求他放过它们的狐狸,这对狐狸是回来报恩的。突出了狐狸的灵性,和知恩图报的狐狸形象。
《额尔古纳河右岸》介绍了鄂温克民族的百年沧桑,同时也呈现出萨满教与萨满文化。萨满是鄂温克族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和文化痕迹,是渗透到鄂温克族生活的最具代表性的民族文化。[4]但是妮浩死后,大家把她跳神用的东西捐到了博物馆,只留下了一个神鼓,本应成为萨满的玛克辛姆没有成为萨满,由此妮浩成为萨满鄂温克最后一位萨满。大部分鄂温克人要去布苏定居,和汉人一起生活,也许随着时间的推移,鄂温克的民族文化会慢慢淡去,甚至消失。
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动物意象的文化内涵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迟子建的代表作,它所包含的动物意象富含了深刻的文化内涵。
一、引言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这篇小说中,迟子建化身为一个九十多岁的鄂温克女人,怀着无比敬畏的心情,用一天的时间叙述了一个民族近百年悠长而又沧桑的历史。翻开这部小说,读者很容易发现,里面存在着一个生机盎然、异彩纷呈的动物世界。它们之中,既有温顺而充满灵性的驯鹿,又有凶残且极具攻击性的野狼;既有神圣而又令人恐惧的黑熊,又有勇猛且富有人性的山鹰……它们是这片具有传奇色彩的土地的一部分,与人一样有灵性,有呼吸。作者赋予了它们种种的人文历史内涵,以寄托自己对社会、对历史及人类的思考和探求。但是对于这些富含深意的动物意象,目前学界却关注甚少。笔者在此力求弥补学界的这一不足,选取小说中作者着墨较多、着重描写的动物意象,以它们为视角,借鉴神话―原型的批评方法,揭示出这些意象所蕴含的民族文化心理及至于整个主题的意义。
二、对传统文明的追忆
悠久而灿烂的中华文明,要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追求“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然而随着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商业气息的入侵,人类赖以生存的和谐家园已遭到严重破坏,人性也遭到严重的异化、扭曲。面对着这渐行渐远的传统文明,迟子建用她那饱含着脉脉温情的笔对它进行了深情的赞美和真挚的呼唤。这种呼唤,不仅是通过人表现出来,在动物身上,也可见一斑。
(一)对自然的崇拜与信仰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作者着力表现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与自然万物的平等相处,自然在她笔下既是人物灵魂栖居的自然,又是被赋予人格情态的自然。如果说把动物作为自然的代表,那么这种情感在它们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驯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驯鹿是生活在大兴安岭一带的人们专门放养的一种动物,作者在书中对它作了专门介绍。它“有着马一样的头,鹿一样的角,驴一样的身躯和牛一样的蹄子”,“性情温顺而富有耐力”,①喜食苔藓,善于在深山密林、沼泽或者是深雪中行走,被人们誉为“林海之舟”。生活在这里的许多少数民族都把驯鹿当做自己的祖先、守护神或者有血缘关系的人,它在小说中一出场便被染上了一种神秘的色彩:
尼都萨满和我父亲一点儿也不像亲兄弟。他们很少在一起说话,狩猎时也从不结伴而行……父亲爱说话,而尼都萨满哪怕是召集乌力楞的人商议事情,说出的话也不过是只言片语。据说只有我出生那天,尼都萨满因为前一天梦见了一只白色的小鹿来到我们的营地,对我的降生就表现出无比的欣喜,喝了很多酒,还跳了舞,跳到篝火中去了。
这段话中的尼都萨满仅仅因为在“我”出生的前一天梦见了一头鹿,原本和父亲很少来往的他竟然主动来到营地为“我”庆生,很少说话的他竟然“喝了很多酒,还跳了舞,跳到篝火中去了”,这足以证明驯鹿作为一种吉祥物在鄂温克人们心中的分量。
不仅如此,驯鹿还是十分有灵性的动物,它和人一样有情感,明事理。如书中提到的一只母鹿,在知道自己的小鹿仔代替生病的列娜死去后,“它一直低头望着曾拴着鹿仔的树根,眼睛里充满了哀伤。从那以后,原本奶汁最旺盛的它奶水就枯竭了”。一次部落搬迁时,“它自动走到列娜身边,温顺地俯下身。列娜什么也没想,顺手就把鞍桥搭在了它身上,骑上去”。后来列娜骑在这匹驯鹿身上时因瞌睡而掉到了地上,冻死了。在列娜追随那只小驯鹿去了那个世界时,母驯鹿又重新有了丰富的奶汁。这样的驯鹿似乎拥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它可以代人死,也可以取走人的性命。鄂温克人对身上所存在的这种非凡的神力是深信不疑的。他们最尊敬的祖先神――玛鲁王是骑在驯鹿身上的;萨满为了使法器有鹿的灵魂力量,常以鹿血荣法器之魂;婴儿患重病请萨满时,必备黑白驯鹿各一只,杀之,以供萨满到天界接回乌麦时骑用……
和驯鹿一样,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一花一鸟在鄂温克人的眼中都具有灵魂,具有神力,所以他们敬畏自然中的任何生灵。这是这种原始的图腾信仰,使得鄂温克人对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是十分关注和爱护的,所以他们所生活的环境总是那么诗情画意,宛若世外桃源。对于这渐行渐远的和谐文化,迟子建用她手中的笔一一将之拾起,呈现在读者眼前,让人无限向往。
(二)与自然和谐相处
正是前面所说的对自然的关爱之情,使得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大自然、大森林不仅是鄂温克人赖以生存和生活的主要载体,而且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与自然互相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也正是前面所说的对自然的.崇敬之情,使得鄂温克人相信,大自然、大森林的动物与植物充满了灵性与神性,它们和人类共同谱写着一曲歌颂和谐生命的赞歌。作为这曲赞歌中一个动人的音符,动物们也向人们传达着来自这个和谐世界的声音。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动物是具有人性的,他们能听懂人类的语言,感知人类的祸福。小说中驯鹿仿佛不是一只动物,而是一个有思想、会思考的活生生的人。它会根据现场判断事情的经过和性质,它会对如何处理事情作出自己的判断,它会为身边人的离去表达自己的哀思。对这样有人性的驯鹿,人们也是平等对待,驯鹿和人之间建立了浓厚的情谊。小说中在描写驯鹿所遭遇的一场瘟疫时,把这种情谊展现得特别真挚、感人:
尼都萨满的脸颊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塌陷了。他黯然无神地穿戴上神衣、神帽、神裙和神裤,为挽救驯鹿而开始了跳神……他足足跳了七八个小时,双脚已经把希楞柱的一块地踏出了一个大坑,他就栽倒在那个坑里。他倒在坑里后毫无声息,不过没有多久,一阵“呜哇呜哇”的哭声响了起来。从尼都萨满的哭声里,我们明白驯鹿在劫难逃了。
那场瘟疫持续了近两个月……达西一看到我们在埋葬驯鹿,就“呜噜噜”地叫,叫得泪水横流。没人理会他的泪水,因为人人的心底都淤积着泪水。
这段文字描写的场面是十分感人的。在驯鹿遭受瘟疫面临死亡时,人们表现的是那样的难过与痛苦。尼都萨满仿佛被击垮一般,“在这场瘟疫中彻底苍老了”,“原本就不爱讲话的他,更加沉默了”。①而平常看似铁心肠的达西在面对死去的驯鹿时,也是那样的悲痛,总是不自主地号啕大哭。试想鄂温克人若不是把驯鹿当做他们中间的一分子,不是把驯鹿当做自己的亲人对待,情又何以至此?对人与驯鹿之间的这种深厚的情谊,读者无不为之动容。一个动物通人性,把动物当人对待的民族,如何能不与自然和谐相处?
三、对现代文明的批判
迟子建在对传统文明中的人性之美、自然之美尽情赞美时,对现代文明中人与自然的异化则表现出强烈的批判,她往往调动一切因素来揭露现实的罪恶。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从“马”这一动物意象身上我们也感受到了迟子建对所谓的现代文明的驳斥与质疑。
在大兴安岭一带生活的少数民族,历史上是不使用马的。小说中鄂温克人所拥有的第一匹马是坤得从俄罗斯人手中换来的。第二次拥有的马是从日本人手中得来的。日本上尉吉田骑着战马来到了他们的部落,他不相信尼都萨满具有神力,于是就和尼都萨满打赌。如果尼都萨满跳神让吉田的伤口愈合,吉田就得把他的战马当牺牲品,让它死去。结果尼都萨满跳完神,吉田的伤口已经愈合,而他的战马也悄然死去。吉田大为震惊,走时留下了另外的两匹战马。达西很喜欢这两匹马,而依芙琳却说:“既然来到我们乌力楞的第一匹马没有给我们带来幸运,这两匹日本人留下的马只会带来灾祸。”果然,依芙琳的话应验了。这匹马导致了拉吉达的死亡。后来,这匹马也给拉吉达的弟弟拉吉米带来了灾难,致使他终身残疾。正因为马给他们带来如此深的伤害,所以后来一个马贩子“带来了四匹马,想要跟我们换两只驯鹿。我们没有跟他做这笔交易。我们不需要马,马给我们带来了痛苦的回忆”。①
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马是一种吉祥物,常作为一种生命力的象征。相传为文化肇始的河图洛书,是由白马驮经驮来外来文化之滋润;《吕氏春秋》中有“马之美者,青龙之匹,遗风之乘”之句;曹操亦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感叹。但是在这篇小说中作者却把它视为一种不祥之物,无疑是有意为之,富含深意。作为外来物的马,就像是入侵的现代文明一样,带给鄂温克人的不是一种美好的生活,而是对他们原有文明的一种破坏,是一种灾难。因此从“马”这个意象上,我们看到了作者对现代文明的驳斥。
四、结语
在中国众多的作家中,迟子建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她游离于任何文学流派、文学群体之外,她总是用她那只笔执著地书写着那个生存在边缘地带的古老民族的传奇历史,吟唱着他们的传奇人生,呼唤着“天人合一”的和谐世界的到来。而《额尔古纳河右岸》所描写的动物,无论是与人们生死相存的驯鹿、给人们带来灾难的马匹,还是勇猛顽强、知恩图报的山鹰,我们亦能从其身上体会到迟子建的创作理念。
《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文化主题
跟随迟子建一同走进《额尔古纳河右岸》,体验鄂温克民族近百年来的历史变迁。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生态环境不断地被破坏,人们的思想也在逐渐的改变,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让我们停一停脚步,反思一下我们的历史,有助于我们能够更从容的走向未来。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是一部非常值得一读的人文类图书,在书中迟子建通过鄂温克民族的历史文化的变迁,向我们展示了人类在社会进程中的尴尬,对于我们的社会进程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民族物质文化主题
一部作品离不开时代与周围环境的影响,一部作品往往记录着我们内心最深处的秘密,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记录了一个民族史诗般的文化旅途,让我们一起走进额尔古纳河,感受不一样的文明,反思当今的社会发展。
1.鄂温克民族的狩猎文化
《额尔古纳河右岸》整部作品都弥漫着苍凉的气息,这部作品可以说是鄂温克民族最后的历史遗迹。这部书开篇则是以女人的视角来看待变迁的鄂温克狩猎文化,女人以其细腻的感受,真挚的感情回忆鄂温克族的狩猎文化,让人感动也让人绝望,这是原始部落文明对于工业文明的无声的控诉。以淡淡悲哀的语调叙述着残酷的历史文明变迁,述说着世代居住的梭罗子变成了白墙红顶的房子,固定的房屋成了鄂温克民族的“坟墓”;习惯了的璀璨星空的夜晚变成了灰蒙蒙的就像被魔障笼罩了的天空,作者有苍凉无奈的描写展现了现代文明对于鄂温克民族文化的损害。
(1)最后的狩猎
鄂温克民族是我国最后的狩猎民族,他们世代居住在大小兴安岭里,他们依靠着山林生存。他们勤劳、善良,他们是最勇敢的猎人。
正如作品开篇则是讲述了林克猎熊的过程,其中充满着鄂温克民族世代传下来的宝贵的经验智慧,写出了鄂温克民族对于山林里动物的生活习性的熟知,那就像是他们身体的一部分,与生俱来。狩猎既是他们生存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神圣的仪式,他们依靠自然生活,他们感谢神灵的赋予。
(2)狩猎的方式
鄂温克民族通常以“乌力楞”作为部落的基本组成,乌力楞中有着严密的组织,他们共同的狩猎,然后进行有组织的分配。其中乌力楞的家族长是由选举产生,一般由最优秀的猎手担任。家族长按照狩猎的季节以及地点的特点组织狩猎,狩猎的方法也就有所不同。
围猎,是鄂温克民族最古老的一种狩猎方式。围猎需要团体作战,因此家族长在围猎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他指挥团体进行有序的包围山头,然后慢慢的缩小包围圈,并且随时关注猎物的动向,然后猎取猎物以后,要根据需求等进行统一分配,保证公平公正,从而带领着整个民族的生存与壮大。
追猎,是一种不分季节的狩猎方式。追猎考验的是鄂温克民族猎人的经验以及智慧,猎人凭借着对于森林中动物的熟知,对其排泄物、足印、毛发、地理环境等判断出猎物的方位,然后凭借着勇气进行追猎,最后捕获猎物。
鄂温克民族世代生活在大小兴安岭中,他们已经发明了很多种的狩猎方式,他们凭借着自己的智慧以及辛勤劳动生存着,然而有一天工业文明到来了。毁坏了山林,摧毁了时代沿袭的生存方式,鄂温克民族就像是一个丢失了魂灵的旅人,游荡在繁华而又迷乱的现代社会中。
2.桦树皮文化
“白桦树是森林中穿着最为亮堂的树。它们披着丝绒一样的白袍子,白袍子上点缀着一朵又一朵黑色的花纹。”这是《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主人公对于白桦树的描绘,可见白桦树在鄂温克族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桦树皮与鄂温克族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桦树皮在鄂温克族人手中被制成各种各样的东西,并且将实用性与艺术性进行了完美的结合。鄂温克族人将桦树皮制成放东西的盒子,或者盛水的桶等等,桦树皮充满了鄂温克族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桦树皮制品充斥在人们的生活中,可以说桦树皮已经成为鄂温克民族的一种文化传承。桦树皮的制作方式仍然有很多在当今社会中流行,它凸显了一种绿色、环保的生存方式。为我们当今社会的科学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萨满教文化主题
宗教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信仰,人们往往依靠着这种精神信仰度过生命中的种种不可思议的困苦。例如,我国的佛教文化、道教文化以及儒家文化给我国千百年来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普通民众带来精神上的慰藉。同样鄂温克民族的.萨满教也支撑着整个民族的生存。《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萨满教的文化主题也是这部作品的灵魂所在。
1.萨满教概述
萨满教是一种原始的宗教,是我国东北宗教的一种统称。在鄂温克民族中萨满既有其宗教价值也有其社会价值。在《额尔古纳河右岸》这部作品中萨满教既担任着鄂温克民族的精神导师的作用,还担任着制定猎物的围猎以及分配等鄂温克民族的发展的作用。另外:“原生性宗教是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把个人体验以及想象的神和神性社会给予集中和筛选,通过世代相传的神话,规范成全社会制度。”可以说萨满教的文化是鄂温克民族的灵魂,是其生存和发展的根基。
2.萨满教的宗教观体现
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带着人性的大爱将萨满文化与鄂温克文化进行融合,从而凸显出鄂温克民族的灵魂。迟子建认为萨满教可以说是自然界通灵的一种媒介。跳大神能够使人起死回生的事情在宗教中是十分常见的,既然自然界中有着无数我们无法参透的奥秘,为什么就不能够默认其存在呢?萨满教的起源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被认为是一种泛神崇拜。
对于灵魂的崇拜。例如《额尔古纳河右岸》开篇中对于熊的灵魂崇拜中写道:“我们崇拜熊,所以吃它的时候,要像乌鸦一样,呀呀呀的叫上一刻,想让熊的灵魂知道,不是人要吃他的肉,而是乌鸦。”萨满教信仰者人为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都有灵魂,因此我们要尊重自然界,要敬畏灵魂。
对于祖先的崇拜。不难理解鄂温克民族世代居住在大小兴安岭中,他们捕猎的技巧、智慧很大一部分源于祖先流传下来的经验,他们沿袭着祖先的生存方式。因此对于祖先他们是感恩的,甚至是崇拜的。所以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作者描写到在氏族搬迁时,由玛鲁王驼载的玛鲁神走在部落的前方。
对于自然神的崇拜。鄂温克民族世代依靠这森林生存,对于自然他们心存感激,是自然神赋予了他们生存的权力。鄂温克民族对于自然神的崇拜非常的广泛,他们崇拜风雨雷电、山川河流等等。然而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自然界的平衡被打破了,人类面临着自然神的愤怒。这是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中》对于当今社会生态环境破坏的深层次的思考。
三、《额尔古纳河右岸》生态文化主题
《额尔古纳河右岸》通过对鄂温克民族的生活的描写,向我们展现了鄂温克民族的生活方式以及宗教信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和谐的生态环境下的民族的生存发展的历程,让我们对于现代社会的生态环境进行深入的思考。
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都是我们千百年来所关注的问题。自从工业革命以来,我们人类一直以自然地主宰者自居。我们任意的砍伐森林,我们肆意的排放污染的废水、废气,我们控制自然,我们主宰自然,因此让我们的贪欲不断的壮大,从而使得如今的社会乌烟瘴气。《额尔古纳河右岸》可以说是迟子建的一种精神上的故乡。他用泣血的手笔,悲哀的语调讲述鄂温克族在工业革命中走向末路的原始文明。鄂温克族人在自然中狩猎,在萨满文化中崇拜自然,他们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同样享受着自然地馈赠,他们在与自然地和谐共处中得以生存发展。
结束语:
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的丰富的物质产品,满足了人们的日常需求,可是也带来了生态的破坏,我们生活的空间不断地被损坏,我们的生活质量也在寸步难行。面对着畸形发展的社会生活,让我们一起将目光投向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感受鄂温克民族的原始文化,深思当下社会的长远健康发展,让我们的社会走向科学发展的道路。
文化视野下的《额尔古纳河右岸》
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以一个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的妻子之口讲述了鄂温克民族百年的盛衰历史。
迟子建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与其说是一部小说,不如说是一部鄂温克族百年来的苦困和文化的变迁史。小说一第一人称“我”——个鄂温克族最后一位酋长的妻子,一个近九十岁的女人,讲述了一个民族近百年所经历的民族变迁史。作者在字里行间都袒露着对这个弱小民族的尊重与热爱,对个人命运和族群命运的关注使迟子建更加关注在未来的发展道路上,鄂温克族如何在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矛盾冲击中找寻一条生存发展之路。《额尔古纳河右岸》为我们展示了它独特的文化魅力,让我们来看看作者是如何表现的,也让我们思考这个即将消亡的民族文化的未来会如何。
一 独特的民族民间文化的渗透
迟子建在写这部小说之前对鄂温克族的历史和风俗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她深入到鄂温克人的生活中,喝着他们的驯鹿奶茶,听着他们的古老的传说故事,体验着他们游牧生活,让作者更加深入的理解这个部族,在绵绵的文字中展示着他们独特的民族文化魅力。
一个民族的文化总是无意识的渗透到他们的生活中,作者从民间视角和世俗关怀的角度,从鄂温克人普通的日常生活中呈现他们的文化。鄂温克人在长久的游牧生活中养成了独特的生活方式,在那古老的原始森林中,他们喝驯鹿奶和桦树汁,男子在外打猎,女子则熟皮子,制肉干,缝制衣服鞋子,坐的是由桦树皮做的'“佳乌”船,住的是松木搭成的适合搬迁的“希楞柱”,女人在月经是用晒干的柳树皮制得丝绒垫在身下,他们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总结了很多经验,如用盐地来和鹿哨来吸引驯鹿,通过树上蘑菇所处的位置高低来判断同年冬雪的大小。他们有自己的小群体,一个部族是一个乌力楞,是有血缘关系的一家人,有部族首领带领,当一个地方的驯鹿吃的苔藓完了后,迁徙到别的地方,由部族首领带领完成一系列的生活事宜。此外还有很多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仪式,如狩猎前后的仪式,婚礼的主持,女人生产时搭建“亚塔珠”,独有的风葬习俗,这些在现代人看来新鲜甚至原始的日常生活却已经渗透到了鄂温克族人的血液中。
迟子建在小说创作中真切感受着民族文化的丰富性和神秘性,充分展示了鄂温克人独特的狩猎文化、路标文化、宗教文化、迁居文化、驯鹿文化,熊和火的崇拜,其中最具特色的是他们的信仰——萨满文化。萨满文化渗透在他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生病时有萨满跳神治病;驯鹿发生瘟疫时有萨满跳神驱邪;婚礼和葬礼有萨满主持;发生火灾时有萨满跳神祈雨。萨满文化中饱含着正义和自我牺牲精神,日伪统治时期有萨满跳神杀死日本战马;森林大火时有萨满跳神牺牲自己性命跳神祈雨,作者对萨满的这种牺牲精神和高尚人格进行了详细的记录。萨满文化是有其神秘性的,它相信神灵的存在,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鄂温克人敬畏自然,相信大自然是有灵性的,动植物和人一样是神灵赐予的,自然的万物都是他们的伙伴,包括他们自己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每一座山,每一条河流都被他们赋予生命的含义,即使是被俘获的猎物也会举行仪式祈求其原谅再食用,他们给所有的生命应有的尊重。终年生活在原始森林中,与大自然有四季更替的规律一样,他们的生活也有了轮回重生的性质。所以作品中死亡不再浓墨重彩,而是随时会发生的事情,因为如同大自然的循环再生,死亡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有死亡才有再生,才能达到生态的平衡。
迟子建是一个对大自然有着热烈情感的作家,她说:“我觉得自然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一直认为,大自然是这世界上真正不朽的东西,它有呼吸,有灵性,往往会使你与它产生共鸣。”不需要用什么标准来判断或评价鄂温克族生活和信仰的正确与否,那才是他们真实的生活,这或许是作者在现代文明充斥的夹缝中看到的那缕自然之光。
二 《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文化立场
小说中,作者是以一个异文化者的身份来看待这个弱小民族的兴衰,这个跨文化的视角使作者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文章也保持客观、理性的色彩。
作为整个社会的一部分,就算是再远离主流文化,也会受到大环境的影响,所以鄂温克族无可避免的会受到现代文化的影响。外部的物质文明不断进入鄂温克人的生活,淘金、伐木、苏联商人的进山交易、日本的侵略,到后来的新中国成立电影和电视采访对其的曝光,都在一点点地影响他们的生活甚至思维。自然的力量是不可估量的,原始的生活方式不断威胁到他们的生命,父亲林克被闪电击中死亡,“我”的第一任丈夫在雪地中冻死,第二任丈夫被熊袭击而亡,在这样的灾难面前他们无能为力,与之相比较,现代的生活有很大的优越性,定居的生活也有一定的稳定性,山下的教育和医疗都比他们原始的要先进,这对新一代的鄂温克人有很大的影响。
外部的世界已经在不断的向前推进,而隔绝于世的这一游牧民族还在遵循着老一辈的伦理道德。文化的闭塞和思想的禁锢让他们产生了许多悲剧。“我”的母亲与伯父尼都萨满之间的爱情就在氏族的陈规陋习中被葬送。因为氏族规定,弟弟去世后,哥哥不能娶弟媳为妻,但是哥哥去世后,弟弟可以娶兄嫂为妻。达马拉与尼都萨满的爱情终究不被认可,最后郁郁而终。而且萨满文化中也有很多不合人性的地方。萨满法师一旦认定,往往会失去很大去正常人一样的资格,他们会为了集体利益而置个人利益于不顾,尼都萨满为杀死日本战马而身死,尼浩萨满为救别人性命而牺牲自己的孩子,亲子的死亡不是一般的伤痛,虽令人动容但有悖于人性,任何人都有生存下去的权利,鄂温克人也渐渐不想在看到类似的悲剧,所以萨满文化会有消亡的一天。
原始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在鄂温克人身上上演。面对现代文化,是坚守传统还是努力适应,是在森林中继续游牧还是下山定居享受现代生活,这些都在决定着鄂温克族的命运。随着下山定居人的增多,信仰的破灭,一个民族也会很快走到尽头,他们独特的文化也将成为遗产。小说的结尾预示着这个民族的命运:“当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消亡的时候,我们连触摸它的机会都没有,最原始的气息都不存在,这是一种悲哀。”面对这一切,迟子建展示了其客观性,一方面这个独特的民族文化的存在不可否认,另一方面在社会不断进步,氏族内部的弊端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原始部落的生活方式终究会不适应发展而被淘汰。这是一种悲哀。但是理想的方式是什么,迟子建表达了她的观点:“人类文明的进程,总是以一些原始生活的永远消失和民间艺术的流失做代价的……诚然,一些古老的生活方式需要改变,但我们在付诸行动的时候,一定不要采取连根拔除、生拉硬拽的方式。……如果一支部落消失了,我希望它完全是自然的原因,而不是人为的因素。”
一种文化能够存在必定有其独特性,它是数代人的传承和沉淀留下了的精华,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所系,《额尔古纳河右岸》就是这样一个文化观念的特别存在。
《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和谐理念
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勾勒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童话世界。
鄂温克人坚持自己万物皆有灵的生活理念,信仰神明、敬畏自然。这与部分“返魅”的思想不谋而合。适当的节制人类无限膨胀的物欲,精神有所皈依,精神有所畏惧,与可持续发展观念有某种相通之处,这对人类重塑精神家园具有某种启示。
“祛魅”(disenchantment)一词,源于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世界的祛魅”(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又译“世界的解咒”,最初的意思是将宗教中的神秘面纱揭开,“把魔力从世界中排除出去(the Elimination of the World)”,韦伯将其具体解释为“拒绝将圣餐中将象征着自己的血和肉的酒和面包分给门徒,这样他们就能在自己殉道以后得到拯救,拒绝这种宗教说教也是一种祛魅”。
美国当代哲学家大卫雷格里芬提倡部分的“返魅”(reenchantment)。他说:“自然被看做是僵死的东西,它是由无生气的物体构成的,没有生命的神性在里面。这种‘自然的死亡’导致各种各样灾难性的后果”。魅,在新华字典中的解释是:形声。字从鬼,从未,未亦声。“未”意为“枝叶招展,花香袭人”,引申为“外貌讨人喜欢”。“鬼”指阴间的人。“鬼”与“未”联合起来表示“外貌讨人喜欢的鬼”。本义:貌美的鬼。汉语中魅字本身就充满了神秘感和未知性,没人知道鬼长什么样,这在无形中给人巨大的想象空间。英语中没有单独“魅”这个词,与之相对应的“enchantment”当“魅力”讲,很长一段时间内“魅”将人类的想象力无限放大,人们将无法解释的现象都归结为魅的范畴,即宗教充满了魅的色彩。然而,当宗教的神权统治束缚了人类的发展时,“祛魅”诞生。本文认为“祛魅”是特定历史时期话语权争夺的一种手段,“祛魅”作为一种消解话语权的理论存在,其主要目的是打破宗教神权的统治,进而发展社会科学,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然而,社会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人类的精神困境并未得到解决。例如,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终极思考始终困扰着人类。因此,“返魅”潮流复苏。“返魅”是“部分恢复自然的神奇性、神圣性和潜在的审美性”,使人对自然有一定的敬畏心理,建立一种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而非人统治自然的霸权理念。
一 追溯精神家园――万物皆有灵
“我生长在大兴安岭,受鄂伦春人‘万物皆有灵’论的影响,我把一花一草,一石一木,都看做是生命的伙伴”。这是桑克《作家迟子建访谈:在厚厚的泥巴后面》中的一段话,用“万物皆有灵”来解释《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创作理念是恰当的。
《额尔古纳河右岸》延续了迟子建多年来的写作意向――寻找精神家园,力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为表达这个主题,感恩自然、一切皆有灵在这部小说中同样充沛。无论山川、林木在小说中皆有神灵庇佑,玛鲁神、火神、山神,甚至较大的猎物熊等,鄂温克人都怀有敬畏,特别是大型猎物一定要经过祭祀才可以吃。在这片被神统治着的区域,古老的鄂温克族过着渔猎的生活,以打猎、放养驯鹿为生,男人从事打猎,女人、小孩对猎物进行处理、采摘野果、给驯鹿挤奶,然而鄂温克人打猎不杀幼崽,烧火只烧失去生命力的树木。他们的生活强调一种和谐的生活方式――人与动物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他们在森林中生活保持着对自然界神明的敬仰,保持了一种原始、朴素的泛神思想,因此对自然的索取存在一种感恩与敬畏,人、动物对自然的索取均在自然界的承受范围内进行,并没有破坏自然界的生态平衡。
然而,文明叩开鄂温克族的大门,打破了这种原始的生存状态――猎民们到山下的激流乡过定居生活,睡在屋子里,而不是可以看到月亮、听到风声的希楞柱;驯鹿开始圈养,而不是自由的寻找食物,它们开始丧失了灵性;有病看医生而不是祈求萨满等,这是文明的侵入,“祛魅”思想的开始。但奇怪的是,在屋子里睡觉使猎民患上了失眠症;驯鹿开始绝食;现代医学也救治不了小达西夫妇的不孕不育。于是,鄂温克人重新回归山林、希楞柱、萨满,“返魅”悄无声息的进行着,“祛魅”被“返魅”战胜。
20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的兴起,将新时期中国文学“返魅”推向新的高潮。在对“寻根文学”有着深远影响的《百年孤独》中,这部小说用“魔幻”替代“魅”,故事的情节发展是按照一个神秘羊皮卷的记载进行的,名字被重复使用,人的命运具有重复性,最终马孔多消失在工业文明入侵的时代。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就有《百年孤独》的影子,老达西死了,小达西诞生,小达西父母不孕不育,在小达西夫妇身上重演等。“返魅”在当代文学中并不少见,韩少功《爸爸爸》将丙仔意象化,古老的陋习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对传统的批判性可见一斑。《额尔古纳河右岸》则不同,他将一种古老的生活传统写得唯美、恬静,让人觉得亲近甚至向往,但作品中最难得的是鄂温克人清醒地认识到“世上哪有世外桃源呢!”体现了这个古老民族对生活的认知与苦难的承受力。这种忍耐与神灵神圣不可侵犯有着很大关系,渎神的人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因此,马粪包在吃熊的时候将熊的骨头乱扔,骨头会卡住他的喉咙。保持对神的敬畏,才会懂得感恩,因此获救后马粪包将自己自宫以示忏悔。至此,“返魅”主题中灵魂有所敬畏在此得到了树立,也解释了人精神家园中神的重要性,揭示了人与自然和谐的主题。正如迟子建自己谈到的,“大自然是这世界上真正不朽的东西。它有呼吸,有灵性,往往会使你与它产生共鸣。”
二 追问终极问题――对死亡的坦然
“祛魅”后的世界将人类的信仰打破,人的精神陷入了无限的虚空之中。渐渐的,人发现了许多科学无法解决的问题――人将如何面对死亡?鄂温克人在面临死亡的时候,近乎于一种浪漫想象――风葬,选择四棵直角相对的大树,砍了些木杆,担在枝桠上,作为一张铺。这样“不用抬头,就能看见太阳和月亮,小松鼠会抱着松塔,跳到她身上和她玩耍”,“人离开了这个世界,是去了另一个世界了。那个世界比我们曾经生活过的世界要幸福”,这种美好的理解使人在面临死亡时不会感觉到无望与恐惧,因为死亡是另一个美好的开始。《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将死亡化为一种美好的柔情、浪漫。这就是信仰的力量,也是“返魅”的力量。 迟子建在谈到他的《伪满洲国》的时候说,萨满能在跳神时让病入膏肓的人起死回生等,大自然中有很多我们还未探知的奥秘,因此不能把萨满的存在看成一种“虚妄”。而到了《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迟子建把这种对于死亡坦然的态度描绘到了极致,“他们在面临着瘟疫、疾病、死亡中所体现的那种镇定、从容和义无反顾,是这支以放养驯鹿为生的鄂温克人身上最典型的特征。写他们的时候,想象肯定是苍白的,因为从我掌握的资料来看,他们本身的经历就是一段连着一段的传奇。”
谈到死亡,不能绕开迟子建在丈夫去世后完成的一部长篇《越过云层的晴朗》,这部小说讲述了“祛魅”后的社会,人们没有信仰,社会变迁给各个人物命运带来的种种不测。没有了敬畏,女儿出卖了父亲,为了获得救赎,她不断地帮助不能生育、将死之人生孩子,以求维持一个家庭的存在,最终女孩死于难产;医生将自己隐藏于深山老林,给人做整形手术为生,但只是改变人的外貌,而无法拯救人的内心,最终医生被精神病人用枪杀死,没人为其讨回公道。“祛魅”后的世界,死亡是令人害怕恐惧的冷冰事情。
“祛魅”给人无畏的勇气,却也给人带到更大的虚无,填补这种精神空虚就是“返魅”。因此,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迟子建酣畅淋漓地抒写了“返魅”给人灵魂的依偎。灵魂有所依附,精神有所敬畏,人在面临死亡会有一种平静与归宿感。伊芙琳在自己老去的时候,开始吃花瓣为生,似乎是要荡涤尽自己的污浊,她平静地离开了,没有喧闹与惆怅。生与死本身就是一种替代,老达西死了,小达西出生了;安道尔死了,安草儿继续着安道尔的愚痴;马伊堪死了,留下西班继续陪着拉吉米等,这一系列的生与死构成了平衡关系,即生即死,同样也是自然规律的和谐状态。
三 “返魅”文学与“祛魅”世界――对和谐理念的建构
“祛魅”与“返魅”最大的争议是建立何种社会理念。“祛魅”是伴随着启蒙主义应运而生的,他诞生的背景是需要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打破旧有的社会统治阶级,与教会、统治者争夺话语权,“祛魅”对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了精神的依据。当科技发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依然有很多未知的领域是自然科学无法解释的。膨胀的物质欲望将人的灵魂陷入了极度的自我膨胀之中,如何解决精神危机?“返魅”成为了首选。因此,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迟子建构建出了一幅美轮美奂的和谐生态图景,这并非是她一时兴起。这部作品 “始终保持着一种均匀的创作节奏,一种稳定的美学追求,一种晶莹明亮的`文字品格。”迟子建认为写作“要爱自己脚下的土地,要一点点地挖掘它,感受它的温度,体味它的博大,这样,你就有了‘根’”。迟子建的 “根”正是基于建立一种和谐的、不随波逐流的社会理念,这种理念作为一股清晰的力量,充斥着中国文坛上的主流话语。迟子建笔下恬静的故乡,展现着另一股北国冰封的景象。那里的人们,仿佛生活在童话世界中,用浪漫的视觉来观察这个寒冷的世界。她笔端流淌的不仅仅是北方独有的风光,更是在旷野的东北,一个地域下的人类的生活状态,以及这种适合地域性的人与自然的和谐。
新中国成立以来,尽管面临着“祛魅”的意识形态氛围,一个个“神”被科技之剑摧毁,被工业文明取代。然而,无论是九寨沟的神奇风光,还是神农架的野人传说,亦或者沈从文故居的湘北风光,拥挤的人流彰显“魅”的魅力。对于神秘,原始风貌、异域情调的社会形态的偏好,对于“返魅”的追求仍然构成了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
面对当前的大千世界,在带给人们更大满足的同时又带来了更大的物质与精神的空虚,这个“得”与“失”的循环,构建了“祛魅”与“返魅”的逻辑,在这个逻辑中,迟子建在“生”与“死”、“知”与“未知”、“放纵”与“敬畏”中,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人类在“祛魅”中,欲望无限膨胀、无休止索取,正是造成生态危机的重要因素,而带有敬畏的“返魅”,适当、合理的生活理念,有助于现代人走出物质圈,进入更高层次的生存发展层次。正如迟子建自己所说:“我向往‘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因为那才是真正的文明之境。”
迟子建《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文化主题
一、《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民族物质文化主题
一部作品离不开时代与周围环境的影响,一部作品往往记录着我们内心最深处的秘密,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记录了一个民族史诗般的文化旅途,让我们一起走进额尔古纳河,感受不一样的文明,反思当今的社会发展。
1.鄂温克民族的狩猎文化
《额尔古纳河右岸》整部作品都弥漫着苍凉的气息,这部作品可以说是鄂温克民族最后的历史遗迹。这部书开篇则是以女人的视角来看待变迁的鄂温克狩猎文化,女人以其细腻的感受,真挚的感情回忆鄂温克族的狩猎文化,让人感动也让人绝望,这是原始部落文明对于工业文明的无声的控诉。以淡淡悲哀的语调叙述着残酷的历史文明变迁,述说着世代居住的梭罗子变成了白墙红顶的房子,固定的房屋成了鄂温克民族的“坟墓”;习惯了的璀璨星空的夜晚变成了灰蒙蒙的就像被魔障笼罩了的天空,作者有苍凉无奈的描写展现了现代文明对于鄂温克民族文化的损害。
(1)最后的狩猎
鄂温克民族是我国最后的狩猎民族,他们世代居住在大小兴安岭里,他们依靠着山林生存。他们勤劳、善良,他们是最勇敢的猎人。
正如作品开篇则是讲述了林克猎熊的过程,其中充满着鄂温克民族世代传下来的宝贵的经验智慧,写出了鄂温克民族对于山林里动物的生活习性的熟知,那就像是他们身体的一部分,与生俱来。狩猎既是他们生存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神圣的仪式,他们依靠自然生活,他们感谢神灵的赋予。[1]
(2)狩猎的方式
鄂温克民族通常以“乌力楞”作为部落的基本组成,乌力楞中有着严密的组织,他们共同的狩猎,然后进行有组织的分配。其中乌力楞的家族长是由选举产生,一般由最优秀的猎手担任。家族长按照狩猎的季节以及地点的特点组织狩猎,狩猎的方法也就有所不同。
围猎,是鄂温克民族最古老的一种狩猎方式。围猎需要团体作战,因此家族长在围猎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他指挥团体进行有序的包围山头,然后慢慢的缩小包围圈,并且随时关注猎物的动向,然后猎取猎物以后,要根据需求等进行统一分配,保证公平公正,从而带领着整个民族的生存与壮大。
追猎,是一种不分季节的狩猎方式。追猎考验的是鄂温克民族猎人的经验以及智慧,猎人凭借着对于森林中动物的熟知,对其排泄物、足印、毛发、地理环境等判断出猎物的方位,然后凭借着勇气进行追猎,最后捕获猎物。
鄂温克民族世代生活在大小兴安岭中,他们已经发明了很多种的狩猎方式,他们凭借着自己的智慧以及辛勤劳动生存着,然而有一天工业文明到来了。毁坏了山林,摧毁了时代沿袭的生存方式,鄂温克民族就像是一个丢失了魂灵的旅人,游荡在繁华而又迷乱的现代社会中。[2]
2.桦树皮文化
“白桦树是森林中穿着最为亮堂的树。它们披着丝绒一样的白袍子,白袍子上点缀着一朵又一朵黑色的花纹。”这是《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主人公对于白桦树的描绘,可见白桦树在鄂温克族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桦树皮与鄂温克族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桦树皮在鄂温克族人手中被制成各种各样的东西,并且将实用性与艺术性进行了完美的结合。鄂温克族人将桦树皮制成放东西的盒子,或者盛水的桶等等,桦树皮充满了鄂温克族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桦树皮制品充斥在人们的生活中,可以说桦树皮已经成为鄂温克民族的一种文化传承。桦树皮的制作方式仍然有很多在当今社会中流行,它凸显了一种绿色、环保的生存方式。为我们当今社会的科学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额尔古纳河右岸》的萨满教文化主题
宗教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信仰,人们往往依靠着这种精神信仰度过生命中的种种不可思议的困苦。例如,我国的佛教文化、道教文化以及儒家文化给我国千百年来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普通民众带来精神上的慰藉。同样鄂温克民族的萨满教也支撑着整个民族的生存。《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萨满教的文化主题也是这部作品的灵魂所在。
1.萨满教概述
萨满教是一种原始的宗教,是我国东北宗教的'一种统称。在鄂温克民族中萨满既有其宗教价值也有其社会价值。在《额尔古纳河右岸》这部作品中萨满教既担任着鄂温克民族的精神导师的作用,还担任着制定猎物的围猎以及分配等鄂温克民族的发展的作用。另外:“原生性宗教是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组织,把个人体验以及想象的神和神性社会给予集中和筛选,通过世代相传的神话,规范成全社会制度。”可以说萨满教的文化是鄂温克民族的灵魂,是其生存和发展的根基。
2.萨满教的宗教观体现
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带着人性的大爱将萨满文化与鄂温克文化进行融合,从而凸显出鄂温克民族的灵魂。迟子建认为萨满教可以说是自然界通灵的一种媒介。跳大神能够使人起死回生的事情在宗教中是十分常见的,既然自然界中有着无数我们无法参透的奥秘,为什么就不能够默认其存在呢?萨满教的起源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被认为是一种泛神崇拜。[3] 对于灵魂的崇拜。例如《额尔古纳河右岸》开篇中对于熊的灵魂崇拜中写道:“我们崇拜熊,所以吃它的时候,要像乌鸦一样,呀呀呀的叫上一刻,想让熊的灵魂知道,不是人要吃他的肉,而是乌鸦。”萨满教信仰者人为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都有灵魂,因此我们要尊重自然界,要敬畏灵魂。
对于祖先的崇拜。不难理解鄂温克民族世代居住在大小兴安岭中,他们捕猎的技巧、智慧很大一部分源于祖先流传下来的经验,他们沿袭着祖先的生存方式。因此对于祖先他们是感恩的,甚至是崇拜的。所以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作者描写到在氏族搬迁时,由玛鲁王驼载的玛鲁神走在部落的前方。
对于自然神的崇拜。鄂温克民族世代依靠这森林生存,对于自然他们心存感激,是自然神赋予了他们生存的权力。鄂温克民族对于自然神的崇拜非常的广泛,他们崇拜风雨雷电、山川河流等等。然而随着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自然界的平衡被打破了,人类面临着自然神的愤怒。这是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中》对于当今社会生态环境破坏的深层次的思考。
三、《额尔古纳河右岸》生态文化主题
《额尔古纳河右岸》通过对鄂温克民族的生活的描写,向我们展现了鄂温克民族的生活方式以及宗教信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和谐的生态环境下的民族的生存发展的历程,让我们对于现代社会的生态环境进行深入的思考。
人与自然的关系一直都是我们千百年来所关注的问题。自从工业革命以来,我们人类一直以自然地主宰者自居。我们任意的砍伐森林,我们肆意的排放污染的废水、废气,我们控制自然,我们主宰自然,因此让我们的贪欲不断的壮大,从而使得如今的社会乌烟瘴气。《额尔古纳河右岸》可以说是迟子建的一种精神上的故乡。他用泣血的手笔,悲哀的语调讲述鄂温克族在工业革命中走向末路的原始文明。鄂温克族人在自然中狩猎,在萨满文化中崇拜自然,他们尊重自然、敬畏自然,同样享受着自然地馈赠,他们在与自然地和谐共处中得以生存发展。
结束语:
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的丰富的物质产品,满足了人们的日常需求,可是也带来了生态的破坏,我们生活的空间不断地被损坏,我们的生活质量也在寸步难行。面对着畸形发展的社会生活,让我们一起将目光投向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感受鄂温克民族的原始文化,深思当下社会的长远健康发展,让我们的社会走向科学发展的道路。
★
★
★
★
★
★
★
★
★
★